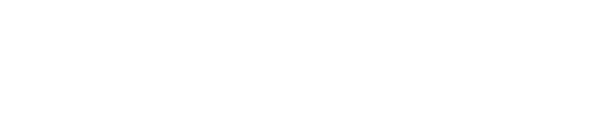作为“茶马古道”和“西南丝绸之路”上的交汇口,下关早在清朝初年便已是大理地区一个重要的村集市场。据载,1723年起,临安(建水)、鹤庆、喜洲、腾冲、丽江、昆明乃至四川的商人便先后前来开店设号,使这个城市一举跃升为大理的商业中心。
我手里有一本《龙尾关老字号》的研究文集,粗略地翻看一下目录,就知道当时的下关在“堆店、旅店”“医药卫生”“文化艺术”“食品加工”“土杂百货”和“加工制造”等各个方面,都已经到了盛极一时的境地。其中不得不说的就是茶叶,下关这个并不产茶的小镇,居然一度成为了西南地区最大的紧压茶叶加工和茶叶交易集散地。1902年,下关的一些茶商在一种被称为“姑娘团茶”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创制成了外圆内凹呈碗臼形的“坨茶”,便是如今驰名海内外的“下关沱茶”的前生。它的创制,不仅解决了茶叶在运输途中容易受损的问题,而且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使之具有一种特殊的内质。一百多年来,这种坨茶通过茶马古道等各种通道,从下关出发,被一匹匹出产于云南大山之间、善行山路、耐力极好的大理马翻山过涧,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人迹罕至的藏区,运送到遥远繁华的京城,运送到省会昆明和天府之国成都,最终在四川泸州广受消费者喜爱,被当地茶商冠以“沱江水,下关茶,香高味醇品质佳”的广告词大肆宣传,最终被定名为“下关沱茶”。
一叶沱茶,足可衬托出下关古镇的商业之盛;一块城砖,亦可沉积出千年古城的历史沧桑。是的,即便从“天宝战争”爆发的751年或754年开始计算,下关的建城历史都早已超过一千二百年。这个活了一千二百岁的时光老人,早就算得上名副其实的“白发之城”。“遗迹悠悠龙尾关,当年盛况洱苍间。”合上书本,念着当代文人创作的一首怀旧小诗,穿行在龙尾关旧城之中,无限的感慨,居然在寿康楼上的几幅匾牌之前戛然而止:“南天屏障”“龙关锁轮”“龙关夕照”“龙关重地”。是的,再多的感慨,在这一块块经历历史沧桑、历练人间智慧的题匾之前也才尽词穷。
的确,古城低矮的民居,沉积着一千二百余年的沧桑历史和无穷智慧,放眼观望,河滨海岸,密密挨挨拔地而起的高楼,十层二十层三十层,哪怕高入云天,还有连区连片的开发区,开阔坦荡,却很难追溯至十年以上的时光。
于是,喜欢怀旧的下关人,喜欢在轻闲的时间回到古城,在龙尾关遗址附近甚至黑龙桥直至西大街和很多老街老巷里,在那些门面不大房舍陈旧的古摊古店中,细细寻找和品咂着当年的旧味,“凉鸡米线”“李氏烤肉”“杜氏汤圆”“黑龙桥包子”“喜洲粑粑”“老面馒头”“过桥米线”“砂锅酸辣鱼”……只有再次吃到这些饱含岁月积淀的味道,才能重新拾回一个个记忆犹新的过往时光。
是的,下关人喜欢怀旧。我也常常感叹,在这样一个人口五六十万,并且以外来人口居多的小城市,如果没有一些所谓古色古香的时代旧气,它就只能确确实实地和那些新兴的城市一起“千城一面”,毫无特点。
但是,即便是“站口小驿”的下关,即便是浮躁不安的下关,都不是这样的城市,她有她的旧色和深度。就比如说久住下关的人,就特别会过日子,与“铁公机”站点上那些行色匆匆的过客,还有被那些大小车辆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焦急万分的驾驶者,以及每天四次以上从公交车上挤上挤下往返于老城区和开发区之间的上班人,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气度和心境,甚至能和久居大理古城的人一样,慢慢悠悠地轻闲着、生活着、安静着、享受着。
当然,这样的气度和心境,必须有时间的积淀和文化的涵养,两者互为弥补,缺一不可。下关老城不缺历史,一千二百年的时光累积沉淀,足够成就这种沉静安逸的气度。同样,下关也不缺文化,在大理“文献名邦”的辉映下,下关依旧文化源远。人们厚教重学,特别是近代,这里就有办学历史上超过一百年的学校:大理师范(现更名为大理州实验中学),也还有办学历史已逾七十年的下关一中,以及全省州市级城市中的首个本科类院校:大理医学院(后并入大理学院,今为大理大学)。
而且,很早以前,下关就以一种海纳百川的态度,接纳着各种文化,包容共生,这里有天主教堂,有道观,有佛坛、孔庙、本主庙,还有清真寺。所以,文化的涵养,使下关并不缺乏厚实的气度。但这样的气度,也只有到了老城区,你才能看得细致,感受得真切。在那一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下,或是在老州政府门前的礼堂广场,还有人民公园的石凳上,还有西洱河两岸的杨柳树下,你才能清楚地看到,那么多习惯遛鸟、习惯闲走的闲适心境;或是稍远一些,到洱河近海口的港湾或是团山的海心亭,那些不论春夏秋冬,习惯游水娱乐的生活方式;还有就在这长长一条河滨湖湾,常常戴个硕大的遮阳帽子,撑着鱼竿垂钓江河的自在心情。